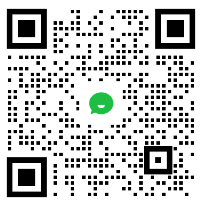在冠以“史上最难就业季”的2013年,699万大学毕业生已经先后离开学校踏入社会。高等教育市场化以来,整个社会留给底层有志青年的升迁道路反而更幽暗狭窄。置身于日益低落的就业环境,蒋泥的长篇小说《今年毕业》贡献给读者的是惊心动魄的审美体验,和意味深长的人文思索。
小说主人公胡炜,是来自苏州农村的燕京大学新闻学硕士,他勤奋刻苦,志向远大,凭着优异成绩连同一箱茅台酒的高昂代价,提前落实了就业单位。这箱茅台酒是他花费几年兼职打工赚来的血汗钱,贡献给就业单位——某大型国营企业总经理乔乐万。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临近毕业的关键时刻,正在就业单位充当实习生的胡炜,无意中撞见乔乐万与干女儿姚瑶在办公室调情,被乔乐万一怒之下断送了前程。“人生给他上的第一节大课,非但不是教科书上说的,要诚实、公正地处世待人,反而是背信弃义、尔虞我诈。”
陷入绝境的胡炜,联想到师兄让他在寻找就业单位时“一定要脚踩多条船,能找几个婆家就找几个婆家,不怕多,多多益善”的忠告,开始在寻求就业和追逐女性方面展开“脚踩多条船”的绝地反击。不曾想他所有的努力,都像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一样,注定要在某部局长严楚升、商界巨头乔乐万、燕京大学副校长单某所共同编织的横跨政、商、学三界的关系网络中四处碰壁、一无所获。
对于来自草根底层、26岁还没有亲近过女色的有志青年胡炜来说,与同校金融系本科毕业生乔雨也就是乔乐万女儿逢场作戏的一夜情,激活唤醒了他原始强健的本能情欲。亢奋中的胡炜,甚至一度涌现出中国传统男权儒生一夫多妻的变态野心:“宁叫天下人负我,不叫我负天下人——就这样,同时追,谁定了和谁,要不两个都要。《聊斋》里不都是二女配一男吗?不能再傻了!”
这里所说的“二女”,指的是乔乐万的亲生女儿乔雨和干女儿姚瑶。事实上,在乔雨的心目中,胡炜只是她逢场作戏发泄性欲的一条“狼狗”:“这一段时间恰想要条‘狼狗’,发现胡炜还有点兽样子,比起城里纯粹的狗种,他皮实,浑身焕发野性,有点乡土的气息。她很想换换味,尝尝新,才肯让他亲近。”
22岁的南方美女姚瑶,与胡炜一样来自草根底层。尽管与胡炜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但是,她更加需要的是以出卖青春美貌为代价来换取尽快改变底层命运的人生捷径。“她觉得这个社会,人活命的成本太高。每一步跨出去,都是门槛,都是沟堑……它不肯设计成一条平直、无障碍的马路,任大家信马由缰。”于是,姚瑶选择投靠了第一任干爹乔乐万,随后又攀附上第二任干爹、著名导演吴雨森,从而通过饰演大型电视连续剧《戏说康熙》的女一号,一举成为一线明星。
与乔雨和姚瑶不同,单校长33岁的大龄女儿单琴琴,一开始就把胡炜当作未婚夫来加以扶持与掌控。作为局长兼《自由谭》杂志社社长严楚升从部里点名带来的唯一助手,她主动给胡炜提供了到杂志社就业的宝贵机会,并且义无反顾地奉献了自己“肉嘟嘟,圆滚滚,右边脸上挨鼻子处有一颗疣子”的胴体。
但是,心高气傲、价值混乱的胡炜,并不甘心付出对等代价:“胡炜感觉把命运系在这么个大女人身上,有点开玩笑,可现实恰如此滑稽。倘若社会是一根竹竿的话,他没有那种要一节节往上爬,爬到最尖端或某个高层去的强烈欲望,但最起码的东西要能保证和把握,这就是竞赛规则的透明化、公开化,所有人在这些规则面前一律平等。那样的话,人们方知道该干什么、能干什么、怎么去干,相应地也便知道了什么是不该干、不能干的。没有了这个,一切在潜规则、暗箱里操作,谁清楚怎样来适应社会,学习、遵守社会的游戏规则呢?于是有了铤而走险的、浑水摸鱼的、落井下石的、不学无术的、巧取豪夺的,无恶不作的……”
对于无钱无势的草根异乡人来说,北京实在让你“又爱又恨”。这里有太多的机会和诱惑,又有太多的歧视与隔离。在没有最为基本的契约平等、权限明确、双向互惠的刚性规则和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弱势一方单边片面走捷径的背信弃义,换来的必然是既害人又害己的双重伤害。初步就业的胡炜,在单副校长亲自出面干预的情况下,被局长严楚升勒令下岗,档案打回人才市场,“连新生活的起点和希望都破灭了”。
将近一年的时间匆匆过去,已经大红大紫的姚瑶终于想到曾经患难与共的胡炜。她辗转找到胡炜,两个人激情迸发,却被包养姚瑶的严楚升儿子严万宝当场捉奸。胡炜冥冥之中再一次扮演害人害己的灾星角色,打碎了姚瑶更加辉煌的明星梦想。借用文学评论家王干的话说,蒋泥的这部长篇小说,“通过毕业找工作这样一个几乎人人经历过的过程,放大了青春被催熟的烦恼、忧懑、残酷,小说在形式上颇费心思。语言也时不时露出《围城》式的幽默和滑稽来,读后令人啼笑皆非。”
蒋泥自己也在代后记《我曾夜夜惊心》中表白说:“最近三年,我曾面试过数十位博士、硕士,他们在职业、户口、薪水、爱好、专长之间,无一不苦恼、彷徨,对前途无可自主,忧心忡忡。专业能对口的,薪酬少;薪酬多了,不解决户口;解决户口的,又是自己根本陌生的岗位……今天的学子另有自己的机遇和不幸,不少被逼上绝境,让我想起十二年前,自己求学、择业时的夜夜惊心。”
应该说,在主人公胡炜身上,是有着蒋泥自叙传式的真切印记的。正是因为蒋泥曾经有过与胡炜一样刻骨铭心、夜夜惊心的求职经历,在处理胡炜脚踩多只船的求职心理及情欲追求方面,表现得入木三分、游刃有余、大开大合、惊心动魄。通读下来,给人以酣畅淋漓、啼笑皆非的审美快感。
就整部小说而言,较为明显的一处败笔,是第33页用较大篇幅让严楚升局长“卖弄”并不高深的白酒知识,第35页又让单副校大段宣讲并不精粹的麻将文化,使得需要快速进入的故事情节,一度被干扰中断。
诸如此类炫耀性的人物对话,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了《红楼梦》的病毒,又上了刘再复、李泽厚的恶当。《红楼梦》的百科全书般面面俱到、一咏三叹的描写铺陈和炫耀展示,所匹配的是农耕时代单边片面地自我陶醉、自我欣赏的慢生活、慢消费、慢节奏;与当下都市男女信息化、快节奏、全方位的就业竞争和情爱追逐,在整体上是不能匹配的。刘再复、李泽厚宣扬的与现代工商契约文明整体脱轨的所谓“情本位”的“返回古典”,用在表现都市生活方面,更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的路径迷失和价值混乱。在情节处理和情爱描写方面大开大合、大胆露骨的蒋泥,在审美情趣方面竟然迷信于《红楼梦》的慢性“情教”,不能不说是《今年毕业》美中不足的一种缺憾。